芷江受降城变成了牌坊:286亿元法币建城经费,999‰被谁贪墨了?
在湖南芷江县的七里桥,今天依然伫立着一座重建的“芷江受降纪念坊”。这座纪念坊修建于1985年,作为“芷江受降城”原计划的一部分。可惜,曾经这个庞大的工程被深深地腐败吞噬。当初为建设“芷江受降城”所划拨的286亿元法币,本应打造一座宏伟的纪念性建筑,但最后只剩下一块简陋的纪念坊。这背后,蒋中正的政府高官们层层盘剥,将资金贪污殆尽,几乎没有多少钱实际用于工程建设。

这座纪念坊最初被称作“凯旋门”,经过多次修复和翻新,现如今所见的其外观几乎保持不变。坊上的铭文,依旧忠实地复刻了当时重要人物的题字。蒋中正亲自题写的“震古铄今”四字,寓意着这段历史的非凡意义;于右任的“布昭神武”和孙科的“武德长昭”,则是对当时胜利的庆贺和对未来的期许。四根立柱上刻着蒋中正的题联:“克敌受降威加万里,名城揽胜地重千秋。”侧柱的题联出自李宗仁之手,充满了自豪和壮志:“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,受降行大典千秋战史纪名城。”
但是,这些华丽的文字,是否真是蒋中正和李宗仁的亲笔,我们不能完全确认。从笔迹来看,似乎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般完美。而不论这些字是否亲自题写,它们都凸显了当时蒋、李等人对芷江受降城的重视。然而,这个宏伟的计划,最终却变成了一个简陋的纪念坊。这其中的原因,还得追溯到1945年8月21日的“芷江受降”事件。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世界局势发生了转折。中国迅速决定了16个受降区,全面接管日本军队的投降。芷江作为受降区之一,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。那一天,时任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坐镇受降现场,周围是众多高级将领,包括冷欣中将、巴特勒准将等重要人物。王耀武作为湘西雪峰山战役的总指挥,他对这场历史性的事件也有着深刻的记忆。
展开全文
芷江受降的仪式场面颇为严肃和庄重。即使是日军的高层代表,也未能逃避中国军方的威严。亲历者回忆,当时的受降场面比南京的受降更加硬气。中国代表团对日方的态度严峻,日军的投降代表即使行了三次鞠躬,依然无法抚平他们的屈辱感。

受降仪式过后,虽然由于人数众多,宾馆房间极为紧张,大家依然兴奋不已。原本计划一个人住一间的房间,有时要挤上两到三人。王耀武的人缘很好,他的房间甚至容纳了四个人。大家彼此交换着感受,畅谈着胜利的喜悦。时任湖南省主席的王东原提议:“受降地点的房屋和用具应保留原样,作为历史见证。”

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时刻,王东原提出将芷江建设为“受降城”。1947年6月,湖南省政府委派陈誉膺和杨化育制定了详细的设计草案,预算高达286亿元法币。然而,这个巨额预算在腐败的层层剥削下,几乎消失殆尽。根据相关资料,最终到达县政府手中的资金少得可怜。面对这种局面,杨化育虽然万分无奈,但还是誓言要建造一座“凯旋门”来纪念这段历史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芷江受降城的计划最终搁浅,代之而起的是这座纪念坊。而这座纪念坊的建设,也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抗战胜利后政府高官的贪污压制。尽管如此,杨化育仍动员了当地百姓,拆除了城东的城墙,最终将凯旋门修建在了七里桥附近。这个纪念坊如今成为了全球仅有的六座凯旋门之一,其他五座分别位于罗马、柏林、米兰、巴黎和平壤。

有传言说,这座纪念坊的根基长年渗出殷红的液体,似乎在提醒着人们:抗日英灵的鲜血不能白流。这些年,芷江的抗日战争纪念设施逐渐完善,甚至得到了陈纳德遗孀陈香梅的捐款与支持。她的参与,让这座纪念坊更具历史意义,也让更多人铭记那个激烈的岁月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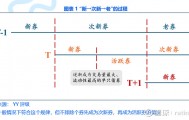



评论